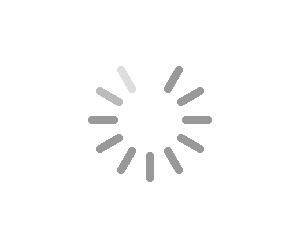来源时间为:2018-01-15
一件事情久了,说的人少了,人们也就慢慢淡忘了,有时简直好像没有发生过,以为是梦景。哪怕是白纸黑字写着的,也以为是梦中的呓语。但有些呓语是不能触动的,一动就痛。这不,现在我就开始痛起来,因一张诗报和一个诗派。
湖南衡阳市的吕宗林君不知是触动了哪根神经,突然说是要写一本《新乡土诗简史》,还在网上开了一个“湖南新乡土诗派研究的博客”,也不知他从哪里知道了我的电话,给我发了短信,说了他的想法。我是知道吕宗林这个名字的,二十年前就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写“新乡土诗”的,而且是“狂热”分子,但从没有联系过,这次算是联系上了。在新乡土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着写诗办报,为新乡土诗呐喊,本应有机会和理由一起喝酒论诗,也不知何故却无缘一见。眼见新乡土诗“烟消火熄”之时,宗林君却从衡阳突然跑到长沙,又是用短信告我,他在某宾馆想与我一叙,就这样,我那根都快麻木的神经就又开始有痛感了。我放下俗务,鬼使神差地奔往宾馆,我们说的就是一张诗报和一个诗派——《诗歌导报》和“新乡土诗派”。
既然宗林君要写“史”,那我当然只能从“史”说起。不过我向宗林说明了,这个“史”只是我眼中的“史”,不一定是“历史”。好在执笔者是宗林君不是我,由他去裁决。
说起新时期的诗歌流派,不能不提到1986年。
1986年,中国诗坛进入了一个社团林立、群雄纷争、流派纷呈、变革迭起的“大摇滚”时代。激情的诗人们,不吝对她进行最热情的礼赞,认为她是中国新诗自1917年诞生以来最繁荣、最兴盛、最灿烂、最辉煌、最开放、最宽容、最自由的诗歌经典时代。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同时各种诗人评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如《星星》诗刊发起的“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人当选。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无疑是《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10月21日至24日,两报先后刊出了总计7个版、64个流派、100多位诗人、13万余字的诗歌作品与宣言。
但是,能够在诗歌史上留下印迹的诗人和诗派却是不多的。以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例,很多人是为了参加这个大展,便宣告成立一个流派,但大展一结束,流派就销声匿迹了。湖南也有胡强和谌林两个诗人参加,他们分别是代表裂变诗派和悲愤诗派参加大展,但这两个诗派也是昙花一现。
“面对狂乱的现代诗潮,任何一位诗人都是不可能平静的,弄潮抑或呛水,高呼抑或轻叹,好像诗人都成了杰出的演员。‘第三代诗人’、‘先锋诗人’、‘前卫诗人’、‘实验诗人’,诸如此类的响当当的招牌在诗坛上穿梭不停。在这一现代诗潮里,确实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海子之仙逝,引起诗坛广泛的喟叹,有人称他是‘北京最杰出的先锋诗人’。海子算一位,大写特写《女人》的翟永明、公然亮出《黑色洞穴》的唐亚军、高呼《你不和我来同居》的伊蕾(孙桂贞)也算。只是翟、唐、伊这3位似乎是‘性诗’的特别顾问,久而久之,读者也就生起厌来。加上这几年,哗众取宠的‘诗派’不少,玩文字游戏的不少。故而,现代诗潮陷入一种困境,一种人为的、也不足为奇的困境。”(陈惠芳《现代诗潮的重大回归》——新乡土诗评述之一,原载《诗歌导报》创刊号,1989年12月)
“一群困兽般的现代派诗人,从搏斗后的黎明中醒来,顾怜着被城市之火烧焦的身影,抚摸着一条条用魔火般的霓虹灯交汇而成的伤痕。他们感到四周都是墙壁,他们开始参拜夕阳,参拜夕阳下那些遗忘过的庄园和童话。”(行人《中国新乡土诗现象沉思录——寻找童话》,原载《诗歌导报》创刊号,1989年12月)
这,就是“新乡土诗”及“新乡土诗派”产生的背景。
“新乡土诗”的概念是由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于1987年提出。“新乡土诗派”是围绕“两栖人”和“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主题性流派。所谓“两栖人”,就是侨居在城市的农民子孙,他们的父辈仍生存在城市之外的村庄。所谓“精神家园”,是指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现在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构筑出的一种精神模型,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的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是以“两栖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社会在自己多重规范的生存空间无法忍受与兑付生命情感时,对朴素、清贫、真诚、健康的美德的回溯。
“我们(指新乡土诗派—笔者注)努力表达的是自然精神与生命精神的谐调过程;新乡土诗无疑有它广阔的前途,它对生命现象和精神家园残酷的真实的追取,以及对一切艺术的精华的崇尚,注定了新乡土诗歌永恒的魅力。”(江堤语)
“我们跟北岛、顾城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成长环境不同,我们从小在乡下长大,不像他们从小就可以看很多书,明白很多东西。我最初看到北岛的诗,非常震撼。仿佛被人重敲了一下,诗还可以这样写?但是北岛做到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到。我们有自己的路子,从我们自身的经历入手,从一种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的处境出发,写我们自己的悲欢惆怅。”(彭国梁语)
正如青年评论家刘清华先生所说,湖南新乡土诗体味的是一种“新乡土精神”。“新乡土精神,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交合体:这是一种既反传统又认同传统,既想寻求超脱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寻根’中寻找思想依托的文化心态。(……)和传统乡土诗不同,新乡土诗人无意于到偏远的乡间去寻求解脱,他们只是把乡村的人和自然万象作为他们观照生活、发掘美的视点和支点。在这里,乡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自然美成了一杆标尺,用以衡量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也许是他们同时意识到了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危机,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被许多人所淡忘了的世界,反过来又给人们创造了一个至善至纯的天地,他们并不想对现实生活作出道德评价,但他们向我们所展示的一切又无时无刻不在引起走向疯狂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反省。(……)在欣赏新乡土诗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受到一种雄性的力度,使我在读他们的诗时为一种正气和激情所驱动,感觉到自我形象也高大起来,让我们不断想起高山的气度、大海的胸怀、草原的骏马、蓝天的雄鹰……其实,这正是新乡土诗作者们所孜孜以求的风格,一种阳刚之美。”(刘清华《湘军中的列兵——新乡土精神与湖南新乡土诗》,引自《新乡土诗派作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对于“新乡土”概念的理解,湖南老诗人于沙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不能把“乡土”这个概念,窒死在乡村和泥土里。不能说,只有那些写一株稻子、一列山脉、一只背篓、一支草笛、一片秋叶、一头黄牛、一块棉花地和一幢吊脚楼的诗,才是乡土诗。也不能说,只有从湿淋淋、滑溜溜的乡间小道,草本丛生、鸟雀吱喳的村落山寨走出来的诗人,才算乡土诗人。乡土,应是一片广阔的疆域。乡土诗,也应该是一个广阔的概念,不只限于农村题材和歌谣体诗。整个中国大地,都在乡土包容之内。只要不是贵族气十足、脂粉气十足和晦涩难懂的古怪气十足,而具有中国诗味、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诗,都是乡土诗。这样的诗,才是中国诗的正宗,中国诗的骄傲,中国诗的希望。(于沙《我观乡土诗》,原载《诗歌导报》第二期,1990年1月)
1988年,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我认识了于沙先生,很快就成为忘年交。经于沙先生介绍,我结识了笔名行人的邢立新,他手里办有一份《青年文学报》,几经往来,趣味相投,我们决定新创办一份诗报。在诗报的定位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当时还只初露端倪的“新乡土诗”上,诗报定名《诗歌导报》。
说到《诗歌导报》,我必须列出一些名字:
顾问:未央、于沙、李元洛、弘征、彭燕郊、谢璞、王以平(第六期始)、黄剑锋、唐大柏、陈白一、姚学礼(第六期始);社长:胡述斌(第一期——第四期为编辑部主任);总编:行人;主编:陈惠芳(第一期——第四期);副主编:高立;编委:胡述斌、行人、陈惠芳(第一期——第四期)、高立、杨林(第一期——第三期)、陈刚、周国清、周正良(第五期始)、苏小河。特邀编辑:江堤、蒋梦(第一期——第四期)、彭国梁(第五期始)
我与行人等人开始筹备《诗歌导报》是在1989年初。当时,他与高立、苏小河等人还在湖南省常德市,而编辑部设在长沙市五家井一条巷七号我的一个师兄家,诗报的印刷却在离长沙五百里的常德市常德彩印厂。
编务工作主要是由我、陈刚、周国清、周正良(还有前期的杨林)负责。那时我是武警长沙指挥学校的一名排级干部,陈刚是武警湖南消防总队的志愿兵(现在叫士官),国清是湖南省军区独立连文书,正良是湖南省军区通讯连炊事班班长。几个行伍之人被缪斯的红裙撩拨得神魂颠倒,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以期一窥春色。而且各自取了笔名,我叫凡溪,陈刚叫山山,国清叫楚人,正良叫宜男,大有一手握枪一手握笔的架式。每当夜深人静,我们处理完当天的编务,也正是饥肠辘辘之时,就会来到正良的炊事班,守着正良亲手为我们炒油油饭,以慰饥肠。二十多年过去,每当忆及此,我便腮有余香。
“请莫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们,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站在生养血肉的土地上,我们是一群生命的游民。从太阳升起的山岭出发,穿过地腹,我们相聚于缪斯的殿堂。为了诗,为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为了友爱和善良,请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们到哪里去。”这是《诗歌导报》的发刊辞《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随着这一声略带忧郁但坚定的低唱,1989年末,在湖南,在冬天,几个不知自己归宿在何处,却又为诗歌寻找归宿的人,为了诗歌的纯真和责任,用几颗温热的心,用几双瘦弱的腿,用几张呆笨的嘴皮,去感染,去奔波,去鼓动。没有经费,他们掏出了准备结婚的积蓄(我将存了三年的九百元钱全部用于《诗歌导报》第一期的印刷费),掏出了准备为儿子买牛奶的硬币(行人的儿子才一岁)。在不知受了多少冷遇(在诗之外都是硬汉子),不知想了多少办法,还不知做了多少违心(不是违背良心)的事之后,终于,全国第一张融诗、影、画为一体的对开大报《诗歌导报》诞生了。这对需要诗歌的良知和爱意的世界来说,对需要诗歌的诚挚的诗人来说,在那诗的多事之秋,也许能多少给些安慰吧。
《诗歌导报》的一声低唱,在全国产生强烈震动,许多诗人、诗评家投书编辑部,给予热切的首肯:
“《诗歌导报》收到,大大的一张,气度不凡。贵报倡导新乡土诗,是顺乎潮流之举,中国新诗在十年的喧嚣之后,也似乎到了一个该沉静下来,走向真正成熟的时候了。我以为,所谓“新乡土诗”,其精髓应是人类家园感与生命意识的沉静式地张扬与触摸。”——陕西秦巴子。
“看来湘军不仅仅于小说,于诗亦是上乘。在目前诗坛日衰之时,仁兄等又有《诗歌导报》,此举令‘九头鸟’们望湘生叹了!诗报不错,有特点(……)我很赞成“回归”观点。”——湖北熊红。
“今天,在小报林立近乎泛滥的中国,见到一如字体那般严肃的《诗歌导报》,不由肃然起敬。浏览了一下诗报,感到‘导向’正,质量高,堪称‘诗歌导报’。在诗坛一派乌合之众的局势下,你们的旗帜使我联想到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旗帜。‘乡土诗’不只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品格、风骨。”——江苏郁斌。
“《诗歌导报》内容丰富,报样大派(……)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们的‘新乡土诗’,感到非常亲切,也感觉到这种回归的趋势。你们的乡土诗,一点也不土,才思敏锐,激情洋溢。”——贵州西篱。
“《诗歌导报》很有大家气质,不妨把画与影的成份再增加一点,办成一张充满艺术气氛的诗报。(……)在屈原的庞大的根系上,我们应该产生新的具有楚地特点的乡土诗作和乡土诗人。”——湖北徐鲁。
“真是意外收获,接到《诗歌导报》真是好高兴啊!你们真有‘两下子’,能办出如此精美大报,而且特别欣赏‘诗影画’。香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