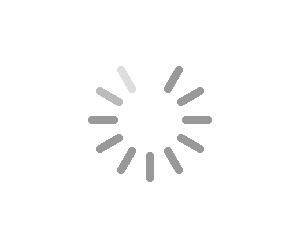李霞生山水画作品
“一位乡村画家和他的‘生态群落’”系列之五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引子
李霞生在北平上学时,画作已达到很高水准。有一次于非
老师看到他画的三棵白菜的条幅,大为赞赏,提笔题上“意在青藤八大之间”八个字。
青藤乃明中期大画家徐渭的号。此人是中国大写意画的宗师,一生郁郁不得志,曾“放浪曲
(niè),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
八大,即八大山人,是清初大画家朱耷的号,此人乃明朝宗室,一生以遗民自居,不与清廷合作,为人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独创阔笔大写意画法,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他画的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他的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则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
青藤、八大影响深远,如齐白石就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
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绘画“能横涂纵抹”,还在于性格自由不羁,不趋炎附势。大约也与绘画这种艺术形式有关,大凡有作为的画家,往往不是循规蹈矩的礼法之士,而是率性而为的性情中人。他们的行为往往“欲如何便如何”,顺从内心情感,超脱功利,不拘泥细节,在一般人眼中,成为“怪人”。
在李霞生的记忆里,京华美专的老师就不乏这样的人。徐燕荪老师到学校上课,有时喜穿军官服装,他说这样坐电车没人敢要车票;他不是没钱买票,而是对当时社会不满,喜好弄鬼。他曾给李霞生画过一张钟馗,上题“社鼠城孤满上都,钟家进士莫何如”的话。
李苦禅性情直率,不擅逢迎,喜怒皆形于色,作画时手上沾了颜色便抹在身上,弄得衣服不整,大衫上红一片黑一片,却浑不在意。
齐白石则拒绝朋友为自己捐官,声言“我如果真的到官场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他不喜欢与官场打交道,甚至厌恶官僚,著名《不倒翁》更是把齐白石对官的厌恶表达得淋漓尽致:“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是心肝。”
李霞生本是率性之人,多年习画,对他的身心更有深刻的影响。这位长期生活在农村,吃玉米面馍、喝糊涂汤就咸菜的老人,颇有逸士风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化馆组织的活动中,他结识了几位同在底层的老书画家,大家情趣相投,长相往来,留下不少逸闻趣事。
20年收徒“不留招儿”
“文化大革命”后期,“运动”有点衰退,找李霞生求画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郭刚庆就曾为人所托,找他要过画。
1975年,郭刚庆结束知青生涯返城,家里地方小住不开,只好借助在同学家。那位同学的父亲——也是他的小学老师,有天突然问他:“你爸认不认识大块镇的画家李霞生?我想请他画几张画。”郭刚庆回家一问,他父亲郭文煊说:“就是你李老伯呀!”
说起李老伯,郭刚庆从小认识,但他不知道李老伯的大名,更不知道这个穿大裆裤、对襟袄的农民是画家。
父亲说:“你去找他吧,记着带纸带颜料。”于是,郭刚庆与同学带着宣纸、颜料、酒和点心去了大块镇小块村。李霞生正在地里干活,家里人去喊,他光着脚回来,知道来意,就拿块毯子在八仙桌上一铺,挥笔画了起来。
这下子,郭刚庆和他的同学开了眼:李霞生运笔纯熟,画得极快,腕底带风,走着画,笔不离纸,不到一个小时,十来张宣纸就画完了。“那画,至今还在我老师家的客厅挂着。”郭刚庆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霞生的画名更是传开了。1980年,新乡县文化馆的冯广滨将他从村里请出来,开办培训班,这年,李霞生已72岁。
1983年,李霞生当年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得以恢复公职,虽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三八干部”待遇,也总算让他出了多年积郁于胸的怨气。
随后,经郭文煊动员,他加入民革,出任河南中山书画院名誉院长,在新乡美术教育方面贡献良多。在生命的最后20年,找他学画的人没断过,从小冀镇到新乡市,很多书画爱好者都跟他学过。他教得尽心尽力,却从来不收学费,顶多让徒弟照顾他起居。他儿子曾劝他:“留几招,你不能把本事教完了。”李霞生笑了:“教都教不会,还留几招?”
三五知己足慰晚年
1980年,冯广滨不只请出了李霞生,他把新乡民间的高人都请了出来,他的家成了这些人聚会的场所。借助这个平台,李霞生与杜汉三、王乃容等人相识,并结为知己。
王乃容是新乡辉县人,河南省京剧团的木工,酷爱书画,自学成才,书画篆刻均佳。那时京剧团经常到各县演出,木工的任务主要是装舞台,到演出他就没事了,开始串文化馆,找人聊天,要报纸练字。王乃容颇有古风,谁要画都给,就是不给官画画。有人请他画了幅画,画完让他题“某某书记留念”,他把画团团扔了:“你不知道我不给官儿画画?书记卖给他了?一辈子都书记?”他很穷,却自得其乐,常对人说:“咱有烟有酒,日子好着呢。”
李霞生很喜欢王乃容,曾攒了路费专程跑郑州看他。那天王乃容因病行动不便,正伏在一张旧桌子上刻章,满桌面都是石头渣子。李霞生问候了他的病情,两人聊了一阵子话,彼此心意畅快,即挥手别过。
杜汉三是新乡小冀镇人,曾是国民党某部少校人事处长,解放战争时期随部起义,在军官教导团培训后,可参加工作也可回家,他选择回乡务农。此后一边种地一边习篆刻,常用的自刻印章为“种菜老汉”、“三十年种菜园丁”。杜汉三极穷,但极大气,与他相识后,李霞生常跑四五十里找他说话。有一次坐上去小冀镇的车才发现囊中羞涩,只得从兜中摸出一幅小品,跟售票员交涉。售票员大喜,收下画把他请到前排的座位上。
杜汉三的家在小冀中街一条陋巷中,房屋是土坯墙,屋内却挂满字画,其中不少是李霞生的作品。一次两人吃饭,有苍蝇萦绕,杜汉三即命李霞生画一只苍蝇落在盘子上,然后自己题上一行字:“识得此中消息,便可官运亨通。”还有一次俩人喝酒喝得开心,李霞生起身说:“咱弄条鱼吃吃吧?”遂在宣纸上急急挥笔,不一会儿,两条鲇鱼跃然纸上,活灵活现。
李霞生与杜汉三言谈不拘形迹,见面往往一个说:“孬货来了?”另一个道:“我来看孬货了。”但他们彼此的厚谊,世间少见。一次李霞生去杜家,到胡同口看到花圈排在两边,大惊,半晌驻足不前。后来看到杜汉三在礼桌前帮人记账,才长舒了一口气。
还有一次两个人都病了,冯广滨、潘长顺、张胜利等人去看杜汉三,杜再三询问,得知李霞生食欲不振,吃饭极少,就挣扎着要家人拿笔墨来。这时他脑瘤手术后不久,只有一只右手能动,就让人在腿上放了块三合板,铺上宣纸,写上“抓紧吃饭”四个大字,题头一行小字:“大孬货霞生听话”,落款则是“二孬货杜汉三赘语”。
“太行山南四皓”画展火爆台湾
晚年的李霞生有两个心愿,一是祖上的房屋被日寇烧了,多年困顿没能力重盖,希望有生之日能建起新房;还有一个是希望出本画集给后人留个念想。
但这两个心愿都不容易实现。此时李霞生名气虽大,画却卖不了多少钱。齐白石在北京明码标价,给钱不够给你画半只虾;李霞生在家乡却不能如此,熟人求画,张不开口要钱,新乡县出去办事,常找他要画,却没有拿钱的习惯。官员去日本,派人找他要画,拿了画就走。他曾无奈地写过一首诗:“自恨画师不知羞,日夜挥毫为应酬。饥饱劳累无人问,老来仍是穷骨头。”
所幸,老人的心愿后来由一名学生帮助实现了。这是他在沁阳国立十三中时的一名学生,叫韩清濂,当年曾参军抗日,后来去了台湾,独创“拓墨画”,在台湾画名很盛,曾在台北、北京、西安以及美国、日本、韩国、巴西举办画展。
1992年,韩清濂回大陆参加“韩愈国际研讨会”,辗转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开始与老师书信来往。得知老师晚年的心愿之后,韩清濂开始谋划让他的作品到台湾展出。在给李霞生的信中,韩清濂写道:
“……台北市有一国父纪念馆,占地极广,建筑之宏伟不亚于北京皇宫大殿,其中设有中山廊。生(韩清濂自指)与其负责人关系颇为密切,如有意在此展出,生有几分把握。惟该画廊只准团体展出,故想邀请豫北一带七十以上老画家(确够水平者)联合展出,如吾师之较大幅者,最少要标价壹万人民币。”
“……普通画家甚难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并且我们这次画展由国父纪念馆馆长,‘中国艺术家联盟’会长、台北市河南同乡会理事长等出面邀请,可谓身价倍增。”
韩清濂动用了自己的全部人脉来办此事,并受汉代“商山四皓”典故的启发,想出一个绝好的创意,他和旅台修武画家葛永祥,李霞生和新乡画家张一圃,四位年过古稀的老画家组成“太行山南四皓”的阵容,最终这个画展在国父纪念馆隆重举行,用韩清濂的话说,“热闹的场面的确非当初始料所及”。
画展结束后,韩清濂将李霞生的卖画所得寄来,个人又拿出900美元。有了这些钱,李霞生在家乡盖了座小楼,出了本个人画集,晚年的两大心愿遂得以完成。
2000年8月14日,李霞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终年92岁。(全文完)
杜汉三为李霞生刻的章
(原标题:流风余韵传留新乡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