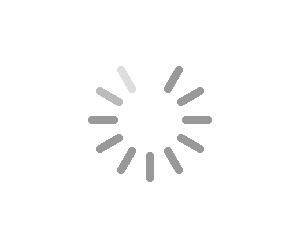传统乡贤在乡村社会的“出场”“在场”“离场”都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实行自治,传统乡贤成为名副其实的治理者。20世纪上半叶以来,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传统乡贤被“污名化”而逐渐“离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新乡贤的“返场”。然而,新乡贤的“返场”不是传统乡贤的简单复活,而是走向符合现代政策的新乡贤。因为党和国家已经给新乡贤的“返场”提供政策空间,并合理限定新乡贤社会角色。为此,重要的结论在于: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不能逾越党和国家的政策空间,必须坚守当下的社会角色的限度。诚然,新乡贤的“返场”也遭遇乡村社会诸多因素的阻碍,需要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促进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道德权威
基金项目:2017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文化权利保障视角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对策研究”(2017sk039)。
作者简介:黄爱教(1979-),男,广西昭平人,哲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300387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措施。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当中,群策群力,把乡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并留住“乡愁”之地?毫无疑问,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农民、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参与其中。在这些群体中,新乡贤显得尤为突出。学者认为,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重要力量之一新乡市(p100-104),是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新变量[2](p101-110)。梳理乡贤研究历史,国内对乡贤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乡绅和绅士的研究,第二阶段是对“新乡贤”的研究[2](p101-110)。当前.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道德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乡贤”进行阐释、解释和界定。尤其在乡村治理、文化建设领域为盛。分析研究新乡贤的学术成果以及考察当前全国各地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新乡贤”评选标准后发现:社会各界对新乡贤的态度是肯定性的。美中不足的是很多人将新乡贤与乡村精英、致富能手、经济能人等同,没有进行适当区分,导致这些评价是一种模糊性的肯定性评价。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如果忽视乡贤固有本性、传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以及当前的国家政策来谈论新乡贤,就会把新乡贤置于不合理的“讨论域”,结果是这样的讨论会进入“不合理”境遇。所以,我们认为,当下讨论新乡贤,必然要厘清传统乡贤的本性以及社会结构,并且讨论新乡贤“返场”的政策空间,才能更好地评估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
一、传统乡贤的理念、比较以及变迁
乡贤从历时性维度来说,分为传统乡贤与新乡贤。本文在讨论概念、理念之时,用的是“乡贤”;在历时性维度分析时,区分传统乡贤和新乡贤。当前学术研究,乡贤更多的指向意义为概念。如果从社会变迁以及文化意义上来说,乡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它是根植于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理念。乡贤作为一种理念,它以社会某种形态为定在,并随着社会不断变迁。
一)乡贤的理念:传统与现代乡贤概念由“乡”与“贤”创造性结合的历史现象,“乡”与“贤”两个概念生态互动和辩证发展的结果,它经历“乡”的“贤”——“贤”于“乡”——走向合一的“乡贤”,形成了乡贤的理念。“乡”字,最初,在甲骨文中表示“二人相向共食”,意为“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后来,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认为“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几经解释和实践,“乡”字从原初的较为密切的人际关系引申到行政区划的概念,指代“在地”“乡邑”“乡里”。“贤”字,在《庄子·徐无鬼》中认为“以财分人之谓贤”,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认为是“贤,多才也”等等,所以,“贤”的意义指向是非常广泛,指代“贤达”“德行高尚的人”。“乡”与“贤”结合为“乡贤”,被指代“在地的贤达”“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当前,很多学者也延续传统乡贤概念,认为“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3]。
但是,“从历史客观存在的乡贤群体来看,被称为乡贤的人主要指的是通过“公议”祭祀于“乡贤祠”中的人物,并不是所有在地的贤达都能被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乡贤”[4](p38-42),之所以这样,重要的原因在于“乡贤”概念还必须经过第二个环节,即“贤”于“乡”。具体而言,贤达在“乡”教化群众、化解纠纷、维持秩序、帮助乡亲、参与事务等而泽被乡里,使乡民受益。经过“公议”,也可以说是承认、认同,才能进入第三个环节,即走向合一的“乡贤”,成为“在地”“乡邑”抑或“乡里”的“道德典范”“精神领袖”以及“村庄秩序的守护者”。显然,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之所以能够成为“乡贤”,并积淀成为一种乡土社会崇尚的理念,需要经过这三个互动的环节。如果按照现代社会学理论来解释,“乡贤”则是一种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动形成的“符号”。作为标志性符号的“乡贤”,由于社会结构、国家政策以及社会观念等差异,传统乡贤与新乡贤的内涵是具有差异性的,如表1。宋代金华府庙学崇祀乡贤情况显示,传统乡贤集中于理学、宦业、忠节、孝义与文苑,并以理学、德行为盛。新乡贤,以2017年河南省[1]首届“新乡贤”为例,主要集中于教育、村干部、文化名人、经济能人,以村干部与经济能人为盛。
二)传统乡贤不同历史形态的比较乡贤理念是历史形成的,就社会学考察而言,“乡”与“贤”概念本身就是变量,是变动的,不同历史时期,传统乡贤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表1中清楚地显示,传统乡贤的功能在于“基层治理”,而传统社会中的乡贤是名副其实的“治理者”,它与“仕”紧密相连,这表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的乡村实行自治,而传统乡贤正是乡村自治的主导者[2](p101-110)。只不过,以科举为分水岭,前科举时代,传统乡贤是取士的重要来源;科举时代,传统乡贤必定是返乡的“仕”。在这里,重要的结论在于:传统乡贤充分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即“一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体的入世文化”[7](p22)。进一步的推论在于:乡贤也必然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契合。
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下,传统乡贤作为实质上的基层治理者,他们必须具有的共同性是:(1)德行。传统乡贤必然以“修身”作为逻辑起点,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才学。传统乡贤必须具备相当的学识,抑或为知识权威,能够以自己的学养造福一方。表现为以知识有效地治理乡里,或兴学授徒、传播知识,教化乡民等。(3)权威。权威是一种获得认同和自愿服从的合法性权力[8](p93)。传统乡贤最显著的特征应当是基于德行、才学等,在乡里获得权威。尤其在乡村治理领域,其作出的决断能够获得认同。就传统乡贤的社会史考察中,他的作用在于承载向上流动、文化传承、知识传统、维系秩序等功能,显然,传统乡贤在“家国一体”结构之中填补了乡村社会的巨大空间,完成“家国”—“社会”的三维结构的建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并不具备黑格尔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环节的“社会”的本性,它仅仅局限于传统乡贤“在地的社会”,它是无“皇权”的“社会”,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乡”的延展不断扩展。在这里,比较“在场”的传统乡贤形态,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上所归纳总结出来的特性。但是,到20世纪初,传统乡贤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被迫逐渐“离场”。
三)传统乡贤的“污名化”与“离场”20世纪上半叶以来,社会变迁深刻影响乡贤的境遇,传统乡贤也经历“污名化”“离场”变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战乱频繁,乡村凋敝,民不聊生,乡村贤达流失严重。进而连年战乱,国库亏空,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权力介入乡村,培植新的代理人并授权其征收税赋,形成“新式地方权威”或“乡村领袖”。这些“新式地方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政权的授权而不是乡民认同,又因为他们横征暴敛,是政府欺压百姓的帮凶,与传统乡贤、乡绅原有的“增进家乡福利和保护家乡利益”等“名节”“名望”相左,所以传统乡贤被污名化。而传统乡贤“污名化”的后果在于“大量乡村贤德人士不愿附和权力,纷纷退出领导权,从而导致乡村社会由土豪劣绅所把持。”[9](p33-37)
然而,“新式地方权威”的土豪劣绅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对象。但是,开明的绅士中国共产党还是欢迎的,延安时期的“三三制”还将其纳入政治体制中[2](p101-110)。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进一步向乡村延伸,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从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瓦解乡绅赖以生存的基础,最终消灭乡绅阶层,乡贤彻底“离场”。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瓦解了地主阶级(乡绅)的经济基础。进而,国家权力在基层进一步强化,推行大规模的集体化,农民生活方式转型,“农民逐渐变成原子化的公民”[10](p243-257),这样的后果在于“冲击甚至直接否定了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和伦理本位”,宗族、家族等各种自治组织力量被消灭,彻底瓦解乡贤的社会根基,传统乡贤在持续的乡村运动中黯然“离场”。
四)新乡贤的“返场”及其问题2014年,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在党和政府倡导下,新乡贤又进入了研究视野。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时过境迁,新乡贤是否还能够“返场”呢?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变化,正如学者认为,“中国亘古及今未有过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从根本上变化了”[11](p3)。但是,“今天的中国,虽然在伦理道德方面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伦理型文化没有根本改变”[12](p4-25)。正是这一点,为乡贤“返场”保留文化生态上的可能,也为乡贤文化提供社会基础。另外,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乡村社会在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工业化等因素影响下,导致文化断裂、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等等。党和国家希望从传统汲取有益养分,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进而,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向中国传统回归,新乡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逐渐走向社会的“自在”,即新乡贤“返场”。必须清楚看到的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性质、制度与政策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党和国家为乡贤的“返场”提供的政策空间如何?这是当下探索乡贤“返场”不可超越的问题。